
via Cominganarchy
I got to level 12 in my 3rd attempt.

A blog on strategies, and applying strategic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related issues, and on miscellaneous discussions about China


上述的观点无疑是西方某传统的货币政策观。可以办 得到吗?地球历史没有成功过。今天欧元币值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多目标」。可不是吗?欧元成立以还,德国与法国的失业率毫无改进,其它的欧盟国家 有失业率低很多的。欧盟之邦有不同的经济困境,是佛利民当年认为欧元行不通的原因,而今天欧元成功,是因为主事者只求币值稳定,不管其它。货币政策的「多 目标」,在实践上没有成功过。原则上行得通吗?理论说很困难,困难重重也:一石多鸟要碰巧。国家大事,岂同儿戏哉?
虽然不是我的研究专业,但自六十年代初期起我跟进货币,有名师指导,同学了得,而后来认识佛利民、夏理·庄 逊、蒙代尔等货币大师,要不跟进也艰难。记忆所及,佛老当年认为没有一个联邦储备局的主席是及格的。后来到了格林斯潘,佛老认为最好。格老的政绩如何呢? 处事临危不乱,国会应对一流。然而,他在任的二十年间,美国的利息率轮上轮落凡八次之多。我早就说过,利息率辘来辘去,辘上辘落,早晚会有投资者或借贷者 被辘瓜。言犹在耳,次按风暴就出现了。
费沙的利息理论说得清楚:投资的回报率应该与市场 的利息率相等。很显然,投资的回报率不可能像格老任内的利息率那样辘上辘落。换言之,格老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违反了经济原则。佛利民当年是反对以利息率调 控经济的,但以币量调控,困难重重,格老转用利率也就无话可说。可惜佛老去年谢世,否则见到今天的次按风暴,足以仰天大笑矣!中国的央行最近加息五次,也 是以利率调控,拜格老为师,放弃了比格老高明的朱镕基传统。不敢说朱老比格老聪明,而是美国的「无锚」(fiat money)货币制度有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佩服蒙代尔,他四十年前就这样说。
西方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起于史密斯之前,其后参与的天才辈出,实证研究的大好文章数之不尽,可谓精英尽出矣。然而,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实践上,该理论有一个无可救药的要点:我们不知道方程式内的货币量究竟是些什么!是M1?是M2?是M3?还有其它吗?
我肯定币量理论有严重的失误,始于一九九五。该年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访港,我带他到雅谷进午餐。在货币研究上,这位师兄非同小可。他是K. Brunner的学生,与老师拍档研究货币得享大名。单以调控银根(base money)来调控币量的主张,是这位师兄一九六三首先提出的。这个「银根」法门后来被西方的国家普遍采用,是以利率调控之前的事了。可以说,从货币理论实证研究的角度衡量,这位师兄的成就不在佛利民之下。
在那次雅谷午餐中,师兄向我提出一个困扰着他的问 题:美元的币量急速上升了好几年,但美国见不到有通胀复苏!他说想不通,唯一的解释是当时美元在国际上强劲。分手后我再想,得到的解释是:一九九一波斯湾 之战后,苏联解体,国际上要持美元者急升,而外间多持美元是不会导致美国本土的通胀上升的。三年前,佛利民直言他对自己多年来的币量观有怀疑,那是大师的 风范了!
于今回顾,我历来敬仰而又拜服的佛利民,币量之说 外,其货币观还有两处失误。其一是他对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解释,是货币的顶级研究,详尽得前无古人,但轻视了当时的美国工会林立,福利大行其道,最 低工资半点也不低。这些加起来约束了劳工合约的选择,而重要的件工合约当时在美国是被判为非法的。我绝不怀疑佛老说的,当年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做错了,失误 频频,币量应加不加,或应加反减,也不怀疑在合约选择自由不足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货币量,搞起一点通胀,对当时的大萧条有助。然而,朱镕基的中国经验却令 人大开眼界。神州大地一九九三的通胀率越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七下降至零,跟着有负三强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速提升,通缩率达两位数字 应无疑问。楼房之价是下降了三分之二的。就是在这样的极为「不景」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而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长三角的经济就是在那时颷 升,只八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重要的经验,明显地否决了佛老的单以货币理论解释大萧条的分析。
佛老的另一项失误,是他认为金本位制度放弃了之 后,一个大国不容易甚至不可以用实物为货币之锚。昔日以金或银为锚的本位制,导致西方太平盛世很长的时日,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向往。可惜此制也,金或银 本身的价格波动会导致其它物价的波动,而这本位制的瓦解,起于经济增长或行军打仗,金或银的供应量不足。
没有谁不同意有实物为本位的货币制度最可取,只是找不到可取的实物。是朱镕基在九十年代处理货币的方法使我霍然而悟,站了起来:以实物为货币之锚,市场要有实物存在,但政府不需要提供实物,而市民是不需要储存有关的实物的。解释是后话。
这里要向周小川先生澄清一下。多目标的货币制度虽然老生常谈,但历史的经验没有成功过。货币的基本用途是作为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 亦即是协助市场交易的单位了。凯恩斯是这样看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的主要目标是稳定物价,而如果只针对这单一目标处理,成功不难。这应该是中央银行要集 中的唯一职责。经济的其它方面应该是央行之外的责任。不要羡慕美国联邦储备的主事者基本上是管到经济的各方面去。看似大权在手,其实手忙脚乱!是那个无锚 的fiat money制度使然。货币无锚,以币量调控物价难于登天,顾此失彼,于是不能不管到多方面的目标去。
君不见,西方常说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开放改革后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是说经济没有波动,而是没有周期性。货币制度不同,市场合约选择的自由度不同,所以有别。个人认为:朱老搞出来的中国货币制度是好的。非常好,要不然中国不会有今天。我同意蒙代尔为此而提出的格言:还没有破坏,不要修理它。
(之四)
---
有数之不尽的理 由一个国家的货币要下一个固定的锚,然后让所有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目前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要解除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外放来纾缓币值上升的压力;另一方 面,这汇管的解除有很大的机会带来不可以接受的高通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几次建议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即是说以一篮子的物品价格指数为人民币之 锚,就更加重要了。
解释过几次,明 白的朋友拍手称善,但好些读者不明白,可能他们想得太深了。不是我的发明。我只是把古老的本位制与朱镕基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知道可行。与一篮子物品挂钩 的想法二十多年前向佛利民提出过,但要等到十年前,得到朱老的政策启示,我才知道提供货币的政府机构是不需要有篮子内的物品在手的。当年大家都想错了。
让我从金本位说 起吧。黄金的本身值钱,以金币作货币,金的所值就是币值。金有重量,携带不便,提供货币的机构可以发行钞票,是纸钞,面额说明可以换取多少重量的金,发钞 的机构是有黄金储备的。这个古老的本位制有两大缺点。其一是金价的波动会导致其它物价的波动,其二是发钞的机构可能遇上黄金储备不足的困难。后者其实是误 解,是错觉,起于发钞的政府或机构营私舞弊,或言而无信,或上下其手。中国清代的一些钱庄与后来国民党的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说明有金或银作本位,都 是骗人的玩意。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的央行再不会那样做,而如果他们那样做,没有谁有理由去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
今天,我们要把 问题倒转过来看。央行发钞,大可说明一百元(或某面值)可以在市场买到某重量的金。短暂的波动当然存在,但可以容许。央行本身不提供金,只是见市场金价上 升,央行把部分钞票收回;见金价下跌,则多发钞票出去,那钞票面值的金量可以稳守。目的只一个:稳守金价,其它货币政策不管。这样稳守就是以黄金作为货币 之锚,也是本位制,是另一种,增加了不需要储备黄金的弹性。容许短暂的金价波动,稳守币值的金价不困难。困难是其它两方面。一、市场的黄金需求或供应可以 大上大落,稳守币值的金量,其它的物价会跟着大幅波动,对经济有不良影响,可以是很坏的。二、市场中的大富君子可以跟政府赌一手,炒金图利。这是说,以市 场的黄金为货币之锚,金量的多少不是问题,其它物价的可能大幅变动才是。
这就带来以一篮 子物品作为货币之锚的建议了。曾经建议用三十种物品,认为不够安全用六十种吧。要选对衣、食、住、行有代表性的,物品的质量要有明确的鉴定准则,要从没有 讨价还价的期货市场及批发市场选择。不难选出约六十种,但再多不容易。篮子内的物品各有各的不同价,比重也不同,而这篮子中的相对物价是自由浮动的。固定 的是一千元人民币(或某面值)可以在市场购得那篮子内指定的物品的质与量,及物品之间的固定比重。最简单是用一个指数处理。说一千元可以购得一个固定的篮 子物品,称指数为一百,央行如果调高指数为一零一,是说要有百分之一的通胀,调低为九十九,是说有百分之一的通缩了。容许每年有上、下限百分之三左右的变 动吧。篮子内的相对物价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对外汇率也自由浮动。篮子内的物品是些什么要公布,每种选哪个市场不一定要公布,而物品的不同比重也不一定要公 布。
这就是了。西方考虑过以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这不成,因为这指数不能直接在市场成交。物价指数只能作为币值的目标,牵涉到不少困难。以「目标」为货币之「锚」不可能固定,算不上是真的锚,是今天西方的fiat money制。 这里提出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可以在市场直接成交的,任何人都可以。央行在明,每天甚至每个小时的篮子内的物价变动清楚,整个篮子的物价指数是随时明确 的。短暂的篮子物价指数波动容许,如果这指数上升过高,央行把部分人民币收回来;如果下跌过多,多放人民币出去。从中国目前的货币运作看,集中于钞票的收 回与放出应该是立竿见影的。最简单是由央行以外币在国际市场处理人民币的交易,而如果外币在国内自由流通(目前差不多),在国内买卖货币对通胀的调控会快 一点。外汇储备那么多,有需要时用很小的一部分足够,何况把人民币外放,有一段时期外汇储备还要急升。
民无信不立。经 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要假设央行不会营私舞弊。这假设容易接受,因为我们没有其它选择!以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无疑会增加人民对央行的信心,而 外间给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消散:汇率自由浮动,你们要对人民币贬值或升值自便吧。主要是与中国竞争的廉价劳力之区,尤其是亚洲一带的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 汇率。大家揾食,懂得做他们的货币会以人民币为锚。另一方面,国内的通胀预期会因为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而烟消云散。
在地球一体化正 在演变的今天,举世的经济形势很不妥。金融(包括股市与国际币值)的大幅波动,半个世纪以来没有见过那么严重。石油之价达百美元一桶,而如果伊朗事发,不 知会升到哪里去。不对头,因为这几年大油田屡被发现。中国呢?屋漏更兼连夜雨,最近深圳推出的约束人民币提款,与明年初举国推出的「新劳动法」,皆令识者 心惊胆战。读者相信吗?不久前两家欧洲机构,说明年起中国会领导世界经济。不知是欣赏还是中伤,树大招风肯定是大忌。
在制度上,中国 还要清理的沙石数之不尽。非清理不可:还有太多太多的同胞的生活水平不可以接受。未富先骄,花巧的经济政策是来得太多太早了。要先稳守然后清理。这几年我 最担心的是人民币的问题,因为只要在货币政策上一子错,其它沙石怎样清理也帮不到多少忙。要一次过地稳定币值,不要管花巧的理论或政策,要把改革的精力集 中在教育、医疗、宗教、言论、法治、知识产权等事项去,大家都知道是沙石很多的。最好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不要管外间的专家怎样说。
是不容易明白的 现象。西方的经济专家云集,但没有政府听他们说的。中国的经济专家数不出几个,但今天却喜欢引进西方的不成气候的非专家经济思维。希望北京的朋友明白,中 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奇迹,方法主要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高斯最近读了我那篇关于中国制度的英语文章,非常欣赏我提到的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试一试,看 一看。」这是中国改革走了近三十年的路,继续这样走下去看来最上算。
(之五·完)
说过多次,反对人民币升值是为了中国的农民。也说过多次,中国农民的生活搞不起,经济增长怎样了不起也没有用。说要改善农民的生活说了几千年,得个「讲」字,但今天是看到曙光了。
近来反对人民币 升值有点火气,情难自禁也。可不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没有改进,或改进得太慢。正相反,大约二○○○年起,中国农民的生活改进得快,上升速度超过我的期望。形 势好,是关键时刻,泼冷水愚不可及。左盘算右盘算,我认为这几年农民生活改进的速度,如果再持续十年——从历史看是很短的时日——中国的农民会达到小康。 还要鼓励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农民生活的改进,是要靠工商业的继续励进带动的。不容易看到农民的生活与城市的人均收入打平,因为后者有大富人家。但农民的人 均收入,要达到城市的中等人家水平不苛求。那是小康,大约还需要十年吧。这是以目前农村的发展速度算,也把二○○三年起农产品价格上升的速度算进去。
说实话,要一下 子大幅提升农民的生活,易过借火。那是拜当年的日本为师,禁止农产品进口。但这样做,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会变得溃不成军,无从再进矣。我反对禁止农产品进 口,或抽进口税;我也反对最低工资,反对补贴农业,反对福利经济——因为这些会扼杀农民自力更生的机会。我赞成大事推广农村子弟的知识教育,认为最好鼓励 私营的慈善机构办学,赞成在农村推广适用于中国的农业科技,也赞成大学取录学生时,农村子弟的高考成绩不妨让个折头。
我也认为两年前取消农业税是对的。这「取消」协助了在农民大量转到工商业去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总量还继续上升:弃置了的农地再被耕耘,雇用全职农工开始盛行,而农作的机械与建设投资,虽然还简陋,是明显地急速上升了。
不要相信农民的 生活愈来愈苦,或贫富两极继续分化。就是北京也难以估计流动人口,以户籍人口算农民的人均收入不对,而外国机构的什么分化指数统计,根本不知道中国发生着 些什么事。在收入的差距上,城市与农村之间可能还在加阔,但相对的百分比升幅,这几年农民比市民升得快是没有疑问的。这发展继续,农民的收入早晚会追上城 市的居民。
北京目前的统 计,是全国农民人口下降至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是以户籍人口算吧。我调查了几个农村(包括河南、江苏、浙江、广东、贵州),图案竟然一样:可工作的农村 劳力,十个走了七个。近城市的走得较少,因为容易半农半工。大略地算一下,从总人口看,今天农村的实际人口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从劳动人口 看,操作农业的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过比较深入调查的专家朋友,说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六年前在广州讲话,我说中国操农作的要下降至总劳动人口百分 之二十左右才算及格。这言论给人痛骂,说永远不可能。曾几何时,今天应该是达到了,比我六年前想象的快。今天看,农作劳动人口再下降五个百分点就差不多 了。
无可置疑,近两 年建筑工人的收入上升得很可观,反映着从农转工的速度缓慢了下来。雇用的农工兴起,而他们的全职收入,目前是略高于工厂的低薪工人。这里要指出一个考虑重 点。以低工资从工商业学起,只要勤奋,知识与日俱增,假以时日,其收入的上限有机会高到天上去。换言之,工商业的知识有很大的争取空间,机会有很大的变 化,因而收入增长的弹性高。农业可没有这样的际遇。中国的农作知识了不起,但主要是数千年的智慧积累,农村的孩子从小耳闻目染,长大后一般都学满了师。不 是说先进的农业科技对中国毫无用处,但地少人多,好些外来的科技没有多大用场。技术上,这些年中国的农业有长进,而以胶布建造温室这几年盛行了。那天我见 到农民投资五千,用胶布建一间房子,可养鸡千只,有无限感慨。是新法饲养,而令我心跳加速的是一户农家拿得出三个五千元。
无论怎样说,一 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加上农业的本质,农民收入的上升弹性远不及工商业。所以我认为一个年轻力壮的农工收入,只略高于工业的低薪是不够的。这几年农产品的价 格比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得快,是好现象。假设工业产品之价不变,农产品之价再升一倍至一倍半,加上设备投资与新技术,农民一般可达小康。这样盘算,我的估 计是再要大约十年。
漫长的黑洞,中 国的农民终于走到尽头,见到光亮了。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出洞口呢?发神经!说过无数次,农转工,中国的农民起步时是转到我称为接单工厂去。这些工厂的产品没 有自己的商标,也没有任何专利,只是有单接单,有版照造,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什么先进之邦,而是越南、印度等工资比中国还要低的地方。人民币升值,大家用 美元结算,订单会容易地跑到这些后起的地区去。今天的中国可没有日本当年那样着数,可以让日圆上升一两倍还有竞争力。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佛利民说得 清楚:世界大变,不久的将来地球会增加十至二十亿的廉价劳力在国际上竞争。没有看错,这竞争出现了,是地球之幸。我为印度、越南等的兴起感到高兴,而对中 国来说,落后之邦有点钱是大吉大利,因为与之贸易可以多赚一点。但让人民币升值是让赛,是轻敌,是未富先骄。
是的,就是农转 工到了一个饱和点,北京还不能让人民币升值。原因是要提升农民的收入,我们要让工商业的收入上升。这上升会自然地迫使工业改进产品的质量与引进科技,而这 几年中国的研究投资的上升率是世界之冠。人民币不升,中国的接单工业总会有抬头的一天。是的,中国早晚要放弃低下的接单工业,让改革较慢起步的接单去吧。 绝对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中国的劳苦大众吃了那么多年苦,今天的形势是他们的血汗换回来的。
五年前说过,人民币强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民大众吃得苦。人民币升值,对富有的炎黄子孙无疑有利。但劳苦大众呢?难道他们会旅游巴黎喝拉图红酒吗?
(之二)
----
上文提到人民币面对两项困境。其一是兑美元上升, 外贸以美元结算,弹性系数不协助,中国的外贸顺差不跌反升。这会带来外间再强迫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一重一重地逼上去,使中国走上日本当年的不幸的路。其 二,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工资,高于跟他们竞争的印度及越南等地,人民币再上升,这几年发展得很有看头的农民生活,会遇到严重的打击。
这里转谈第三项困境。那是这几个月中国的通胀是明 显地上升了,到了近于不可以接受的水平。这里我们要冷静下来,思量一下。首先,近来的通胀加剧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得快。这是好现象。农转工的人数那么 多,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是自然的现象,而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升,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有抬头的一天。然而,普通常识说,农转工的人数多,非农业的物价理应下降才 对。但没有,只是上升得少。原则上,中国的物价指数,农产品占三分之一,其价上升一个百分点,其它物价下降半个百分点可以抵销,使通胀率为零。但没有。在 目前中国的发展中,通胀年率低于五可以接受,目前是在六至七之间,不好,也不大坏。
大坏而又头痛的,是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 按照经济常规,币值上升是会带来通缩的,但没有。以香港为例,近两年港人到大陆消费,物价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强。不是说国内的人也遇到同样的通胀,分析复 杂,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人民币值在国际上升了,国内的通胀率其实不止目前公布的六至七之间。
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币值上升,应该有通缩——读者不妨想象人民币值大幅上升,通缩必至——但为什么上升了百分之十还会有通胀加剧的现象呢?
我的解释有两方面。其一,贸易顺差急升,外资继续 涌进,外汇储备激增,这些进帐或迟或早是要用人民币兑换代替的。这会导致人民币的国内流通量增加。不是说外汇进帐要下降至零才没有通胀,但因为这进帐的激 增使人民币量上升,央行加息约束的主要是国内市民的消费与投资,不是明智之举。其二,央行以压制人民币需求的方法来纾缓其上升压力,例如禁止在国内自由地 以外币兑换人民币,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压制需求会促使市场预期人民币会继续上升,争持人民币会使币量被迫提升。
这就带来我曾经说过的一个重点:要纾缓人民币上升的压力,约束需求(目前做的)是劣着——正着是增加人民币的供应。后者,为避免国内的通胀加剧,央行要把人民币大量地放出国外——这是要解除目前的外汇管制了。
解除汇管,把人民币大量放出去,要人民币变得毫无 上升压力很容易,而放出去够多人民币值是会下降的。要注意:把人民币放出去与此前决定(而最近剎掣)的天津「直通车」到香港买股票很不相同。「直通车」是 内资外流,但人民币外放有引进外汇的效果,国家是有钱赚的。这里要说清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不反对内资外流,但指明是购买股票却是劣着。股票之价,原 则上,是反映着上市公司的回报率,市场应早有定论。无端端因为「直通车」而使港股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反映着股民一般无知,早晚会损手烂脚!买股票不是移民 潮买楼,不是自由行购物,而是市场投资,要看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
炎黄子孙有钱出外投资,那很好,但要让他们自由选择投资的项目与回报的预期。说实话,当今之世,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投资比神州大地更可取,但如果炎黄子孙要分散一点,那到外间下点注,过瘾一下,也无不可,但不要强迫他们通过港股市场。
要纾缓人民币的上升压力,大量把人民币推出国际是 最上选的了。这里还有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重点。这两年人民币上升,主要是兑美元上升,而我说的接单工厂今天叫救命,主要是他们一律以美元结算!是个尴尬的 问题,炎黄子孙很有点面目无光:既为泱泱大国,经济搞了起来,震撼世界,但外国人购买中国货,为什么不能用人民币结算呢?这是因为中国还有汇管,人民币不 自由外放。
北京的朋友要为国家的尊严设想一下吧。但在目前的 形势下,解除汇管让人民币自由外放,有不小的机会带来相当头痛的麻烦:国内的通胀因而急速上升的机会存在。这里我们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有两点对通胀 是有利的。第一点,如果北京依照我的建议,取消进口税,贸易顺差大跌,有纾缓通胀的效果。第二点,以提升人民币的对外供应来减少该币的上升压力,市场再不 争持。另一方面,人民币自由外放,对通胀不利也有两点。第一点,人民币的强势下降的本身,会增加通胀的压力。第二点,如果外放了的人民币回流,国内的人民 币量增加也会导致通胀。人民币留在外地则不会,但外放了的总会有某部分回流,尤其是投资中国这些年成为风气了。我们无从估计外放了的人民币的回流比率会是 多少。
两点会纾缓通胀,两点会增加通胀压力,一起合并, 国内的物价会向哪个方向走呢?很难说。如果一定要我猜一下,我认为在目前的物价明显地趋升的形势下,解除汇管,外放人民币到没有上升压力的那点,国内通胀 加速的机会较高,有可能引起急速通胀。因此,我不能不旧话重提,建议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这后者我分析过多次,但好些读者还是不明白。应该是传统的货 币观误导了他们。我要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一次。
这里要补充一下的,是人民币大量外放,中国的外汇储备会相应上升。与贸易顺差及外资涌进的储备上升不同:除非人民币大量回流,其外放带来的储备上升是不会增加通胀的。
(之三)




(按:此文乃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于贵阳贵州财经学院讲话之大略。是日也,朝雨送寒,午后讲座,老师同学云集者二千。随后挥毫数纸,晚宴贵州茅台,夜叙法国红酒,老生常言该地贫瘠,盖前日事耳。)
各位同学:
我老是想得简单,这次讲话,每点要说的都简单,但因为有多点,加起来就变得复杂了。所以同学们要听得留心,否则加不起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快,历久不衰,其货币币值强劲,在国际上有上升压力,是大吉大利的形势,与货币呈弱势是两回事。好比一个男人找不到女人,相当头痛,但如果有多个美女追求,则过瘾之极,处理何难之有哉?目今人民币在大好形势下遇到不容易解决的困境,恐怕源于处理失误,为何如此,怎样解救,说来话长,让我说说吧。
二○○二年我在南开大学说人民币是天下第一强币(当时黑市还低于官价),二○○三年三月说两年内先进之邦会强迫人民币升值(当时黑市与官价打平)。不出所料,只四个月后这「强迫」就出现了。我当时是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这反对今天依旧——为何反对我会解释。感谢货币大师蒙代尔。他也屡次公开反对人民币升值,后来知道他的理由与我的差不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首先要说的困境,是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六至十之间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急升。说过好几次,货币汇率上升会导致顺差上升的机会很大。经济本科一年级的弹性系数分析,说物价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总消费可能增加。到了三年级的对外贸易课程,这弹性系数增加了好几个,方程式长而复杂,都支持着货币汇率上升不一定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但没有谁可以事前推断弹性系数是哪个数字。当然,如果人民币升得够高,到某个价位中国的贸易顺差一定会下降,但到那一点,或到顺差不存在的那一点,中国的经济很可能会走上日本的路。我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发表《日本大势已去》的。
是的,当年发展得头头是道的日本,经济不景已有二十个年头了。二○○一年在三藩市与佛利民畅谈日本的困境,他说日本看来有转机,六年过去,这转机还看不到。这可能是因为日圆币值在国际上大幅上升了,受益的多是有钱人,话得事。三十年前红极一时的日本,在经济政策上犯了两项大错。其一是禁止农产品进口,使地价急升,飞到天上去。其二是让日圆汇率升值,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升至八十兑一(今天约一百二十兑一)。史坦福一位名教授作过深入研究,两年前发表所得,直指日圆升值对日本经济的祸害。像蒙代尔一样,这位教授支持中国,反对人民币升值。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经济学诺贝尔奖十之八九落在美国学者手上,但那里的议员老是认为人民币值上升会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更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外国坚持要求中国货价上升。说会增加本土的就业机会是浅见。最近见报,中国货的价格在美国是明显地上升了,需求弹性系数低于一,中国货的总消费于是上升了。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我敢十对一打赌,外国施压要人民币再上升必将加剧。另一方面,虽然中国贸易顺差上升的本身不一定会导致人民币值上升,但市场一般是这样看。如此一来,政治施压,市场又施压,人民币要不升很头痛。
不止此也。最头痛的关键,是如果人民币受到压力而再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会继续上升的机会很大。这是因为中国货在外地畅销已有十多年,那里的消费者养成了惯性,这是会促成弹性系数下降的。我们无从知道人民币要升到哪个价位这惯性才会改为有利中国贸易顺差下降的弹性系数。这样,人民币值再上升,中国顺差又再上升,外国加重施压,一重一重地推上去,中国会被迫走上日本的不幸的路。前车可不鉴乎?
只有两个可以改「善」中国贸易顺差(指减少)的途径,肯定有效的。其一是中国大幅施行出口关税。这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极为不利,但总要比外国大幅提升中国货进口税为佳,因为前者税收由中国获取。其二,最佳的选择,是废除外国货进口中国的关税,或起码大幅减少。废除所有进口关税是妙着,最好的,贸易顺差一定下降,而炎黄子孙可以大享鬼子佬的名牌真货之乐矣。不妨考虑与外国洽商,大家一起取消所有关税,但中国单方面取消所有进口税也是正着,何况这后者潇洒好看,干脆利落,有大国之风。这也是对世界公布:地球一体化,我们不跟你们婆婆妈妈,身先士卒地表演一手,成为天下第一个自由贸易大国。
纵观天下大势,我认为中国取消所有进口税不仅要做,而且迫在眉睫,要尽快做。这是一项肯定可以大幅减低中国贸易顺差的法门,而又因为有那么多的外资要到神州大地下注,我们无需担心取消进口税会对中国目前的外汇进帐有不良影响。说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么多,要烧也要烧好几天。
取消进口税对中国的工业会有负面影响吗?也不用担心。一个原因是中国货的竞争者绝大部分不是先进之邦的优质名牌,另一个原因是让优质名牌免了关税杀进中国,这些产品会迫使中国提升产品质量,很快的。今天,我绝不担心中国的工业家会那样不争气,见到外来的名牌就心惊胆战,鸣金收兵,躲起来了。
六年前,在某次讲话中,我说如果举世取消关税,全球一体化竞争产出,我会将身家押在炎黄子孙那边去。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之一)
先說明設定綠色GDP的初衷。中國各級官員的考核升遷裏最主要的考核指標就是GDP的增長。中國過去27年GDP的高速成長,跟考核方式脫不了關係。也正正因為如此,世界上只有中國的GDP裏水分特多。縣虛報一點,到了市級又來個四舍五入或幹脆增加幾個百分點,到了省也一樣。到了中央,才可以勉強往下壓一點,因為國家級幹部考核的指標不完全相同了,而且GDP增長率也已高得不可信了。別的國家地區並沒有這種考核制度,因此也沒人去花這種心思虛報。謠傳上一任的統計局長邱曉華的下臺,就與他收受賄賂,串同虛報GDP有關。上海的陳良宇是其中一個行賄者。由是統計局雖名為局,卻是一個部級的機構,因其責任重大。綠色GDP的用途,就是要在官員考核的方程式裏扣減綠色GDP的損失。
GDP的計算,是經濟學家的範疇。筆者,門外漢也。班門弄斧,勉為之。據說綠色GDP本來要采取類似GDP的框架。於是,就產生了如每噸煤該扣減多少綠色GDP的難題。環境汙染如何難以量化先按下不表;GDP是每年計算的,單位是“元/年”,環境汙染是長期的,單位是“元”。要把兩個不同單位的量相比(或相減)在數學上是不可能的。當然學術上的綠色GDP是存在的,就是體現其總體影響的凈現值(NPV)。可是要達到計算綠色GDP的初衷卻不容易。此為中國綠色GDP推行不了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據說統計局參考了各方學者的研究,其中不合理之處不勝枚舉。例如,有提議把煤的汙染都算到采礦者的頭上。實際上,產煤者只該負責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汙染,而用那種燃煤發電機,如何過濾燃燒產生的廢氣,乃用煤者的責任。目前國家的統計法和資料收集,不足以支持較真實的計算。這是目前國家統計局暫時停止了綠色GDP項目的最主要原因。
This is not to defend Dr. Jin Lei. I am just shocked at the lousiness of the NYT reporting.
IHT and NYT today carried one of the most ignorant and biased articles for such a renowned paper.
Two reporters, David Barboza and Duff Wilson, reported a case against dr. Jin Lei,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Genesci, the market leader of Human Growth Hormone (HGH) and also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ly biotech companies in
A few very important facts seem to have been deliberately missed or mis-directed, which made this reporting look like total trash.
I do not want to defend Dr. Jin and I do not have any knowledge about the case. All I know is that if I were Dr. Jin, the report would suffice a libel suit against IHT and the two reporters. I also believe that sloppy reporting like this will be viewed as part of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in a malicious attack on anything
The story runs in parallel with that of
This is another proof of Barnett’s theory of “economic connectedness”. If situation in


有关中国的绿色GDP,外界一直兴趣颇高。所以到最近统计局确定不会推行绿色GDP时,外界媒体的极度失望是很自然的了。如外界媒体所报道,地方的压力当然是部分的因素。可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绿色GDP计算方法。
先要说明一点,为什么会产生绿色GDP的问题。中国官员(从省到市到县)的考核升迁,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GDP的增长。中国过去27年GDP的高速成长,跟考核方式脱不了关系。也正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只有中国的GDP里水分特多。县虚报一点,到了市级又来个四舍五入或干脆增加几个点,然后是省。到了中央,才可以勉强往下压一点,因为国家级干部考核的指标不完全相同了,不过通常也只是因为GDP增长率高得不可信了。别的国家地区,并没有这种考核制度,因此也没人去花这种心思虚报。谣传上一任的统计局长邱的下台,就与他收受贿赂,窜同虚报GDP有关。上海的陈良宇是其中一个行贿者。由是统计局虽名为局,却是一个部级的机构。因为其责任重大。绿色GDP的用途,就是要在官员考核的方程式里扣减绿色GDP的损失。
GDP的计算,是经济学家的范畴,笔者并不懂。据说绿色GDP本来要采取类似的框架。于是,就产生了每吨煤该扣减多少绿色GDP的难题。如何量化环境污染的难题先按下不表。GDP是每年计算的,单位是“元/年”,环境污染是长期的,单位是“元”。要把两个不同单位的量相比(或相减)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研究一个学术上的绿色GDP,不过这参数难以简单地转变为考核指标,因此达不成原先构想的目标。此为中国绿色GDP推行不了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据说统计局参考了北欧国家和各方学者的研究,计划中绿色GDP的统计算法把煤的污染都算到采矿者的头上。实际上,产煤者只该负责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而用那种燃煤发电机,如何过滤燃烧产生的废气,该是用煤者的责任。目前国家的统计法和资料收集,没法考虑上述因素,因此也不能支持较真实的计算。这是目前国家统计局暂时停止了绿色GDP项目的最主要原因。
至于环境问题如何解决,且听下回分解。

I went to Shanxi for a few days recently (the bonus is to cover one more province in my footprint map). For the interest of time, instead of posting a travelogue, I will just list a few notes to share.
The Brick Kilns
1. People talked to me about the slave kiln voluntarily (before I asked). People I talked to confirmed that this has been widespread for some tim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t least been aware of such things to some degree.
Worse still, there was at least another case of burying a slave alive in Ruicheng County (芮城). I hope if there are journalists who come across this could go there to confirm if this is true. Because if it is indeed the case, that means there have been cover-ups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People (or Mr Wen) will have more ammunition to ask for a thorough review of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bad officials
2. Contrary to the sentiment outside, in general, the local people do not feel that the punishment has been too lenient. I even heard of sympathetic comment about a deputy county mayor who was on the job only for 1 year.
3. On the road, one often see some 'wanderers'. the locals who drove with me told me that many of them were "released" from the kilns, and left to survive by themselves. "release" was actually a euphemism, the kiln owners actually drove them to the middle of nowhere and got rid of them. Since many of these ex-slaves are mentally retarded, they have no idea where they want to go. So they just wandered around.
4. Across the border in Sha'anxi province (陜西), I saw many klins by the freeway as well. I do not know if the situation is similar as it is in Shanxi (山西). But I think this worths a good story to cover for the journalists because
Other observations
6. Many small factories were seen along the coal area (e.g., between Linfen 临汾 and Pingyao 平遥 ). We saw coal everywhere along the river and the rail tracks. Many of these small factories store a lot of coal in their back yard. Apparently, it is cheaper to burn coal for power for them
7. When we passed through Xian 西安,construction was everywhere. It was reminiscent of Pudong in 1996-1997. If you ask me whether China's growth will continue for the next decade, you need to visit these cities. They are undergoing the same dramatic changes as the coastal cities on 10-15 ago. In 10-15 years, Xian will be like Shanghai, Taiyuan will be like Nanjing.
8. We took the cheap cabin train for a large part of our trip, mainly because there is only one cabin class ("Hard seat") available in the schedule. But we also wanted to talk to the average citizens. In a culture where people are shy in talking to strangers the train is perhaps the only exception, this has been so even back in the Mao era (when the society was more close).
On the way, we were inquired twice about the pork price in HK, by two groups of middle age ladies. They said 500g of pork cost 5-7RMB last year and it cost 17.5RMB now. To them pork price is like gasoline price to the American.
I asked my mom when I went back to HK. Apparently she failed to notice the difference. After some questioning,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rice hike was probably less than 50% in HK.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price hike was much more noticeable in Shanxi, because all the cost come from the real cost of "manufacturing" the pork, i.e. rearing. Whereas in HK, or perhaps in coastal province the "value-added" (transportation, middle man, distribution) represent a large portion of the price, which has not changed as dramatically.
(similar observation on the change in gasoline price in US vs HK, while crude oil price hik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percentage increase in US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HK, as the base in HK was much larger.)
Remember this when you visit Hiroshima or Nagasaki next time. Remember the sacrifice of the innocent Japanese who died in August 1945. Remember how many lives they have saved for their own country, and for the world.
Remember Manhattan Project. Remember Oppenheimer. Remember Ein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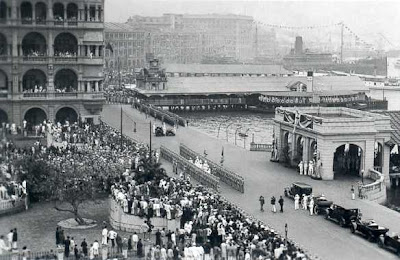
FYI, "asspara" is not a para-para dance with the bottom. it is a vegetable that we all know,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Katagana with some truncation in phonetics and translated back to Engrish again losing some more fidelity. (like compressing a picture file into jpeg and then to gif and back to jpg again -- if that makes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As for "Shrimp and cock soboro hammering out pasta curry cream", I will leave your imagination to figure out what it is.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know how to distinguish male lobsters from female ones, but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identify the same part of the body for shrimps.